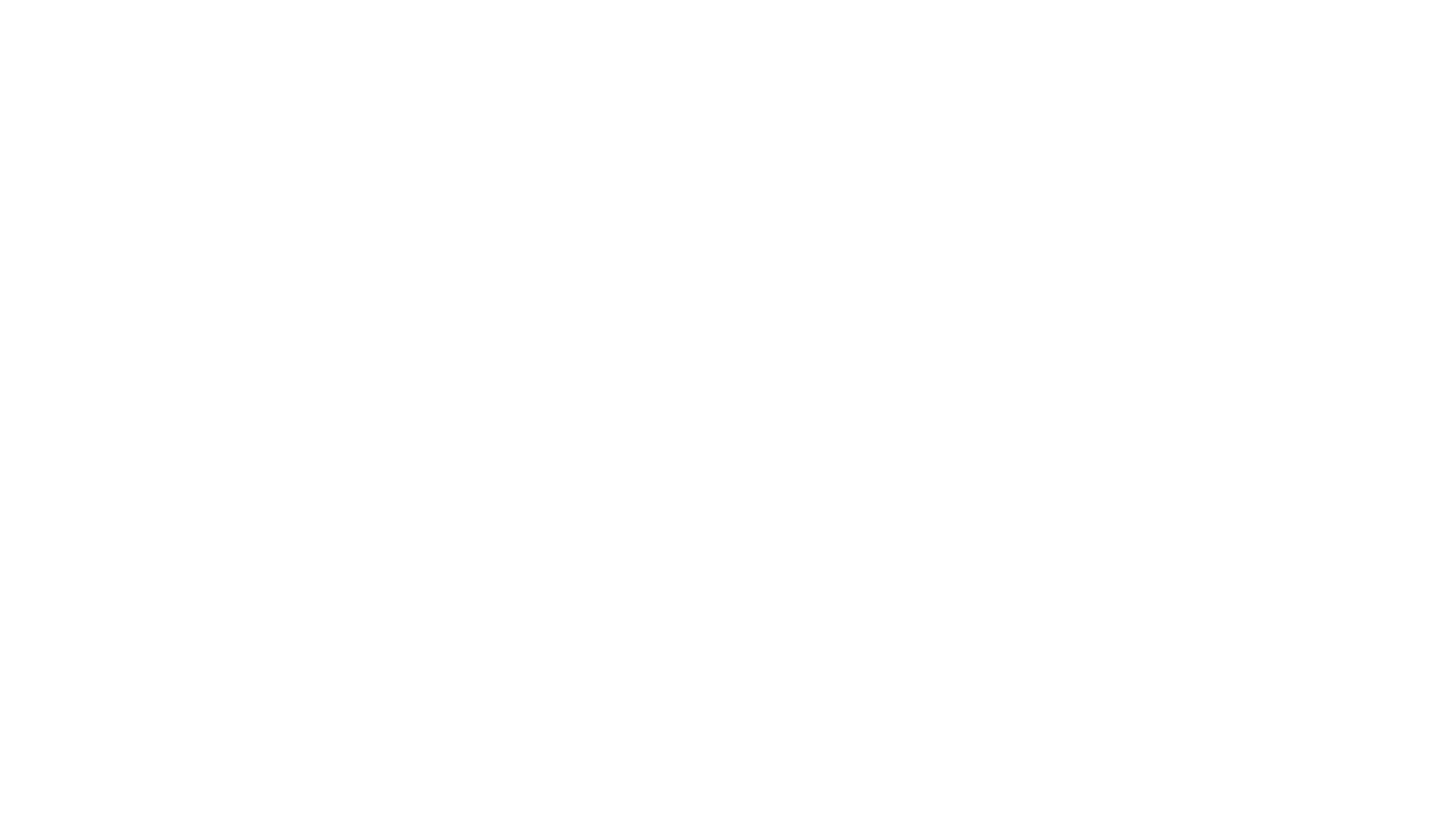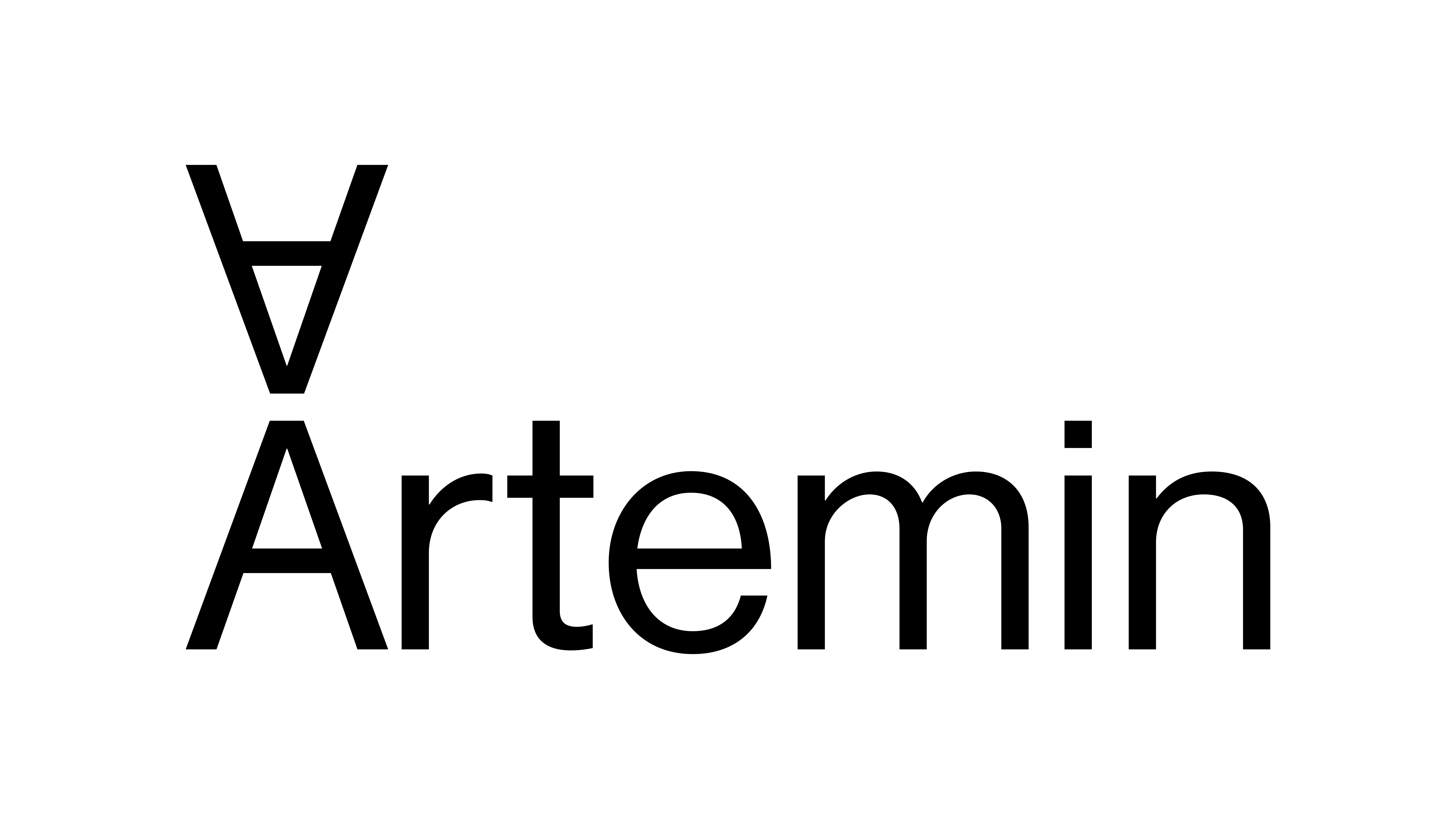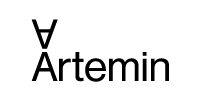INTERVIEW: “Light Filters Through The Gaps In The Leaves” ARTISTS
[ 專訪 ] 藝術家 Jen Hitchings / Stefano Galli / Maria Sainz Rueda / Theresa Möller Artemin Gallery於 2024年4月6日至6月18日舉辦聯展,呈獻Stefano Galli、Jen Hitchings、Theresa
INTERVIEW: SOLITARY WALKS ARTISTS
[ 專訪 ] 藝術家 陳玉純、伏流物件、身體山島 Artemin Gallery 於 2024年2月24日至3月30日舉辦聯展,呈獻陳玉純、伏流物件、身體山島等三位藝術家共24件歷年作品及新作。「藝術家」是一個寬廣的概念──細看三位的創作,各有各的藝術定位和美學堅持,來自於他們各自對藝術與生活的創作態度。 陳玉純 Yu-Chun Chen 陳玉純 (1980-) 經常沿著海岸漫步或騎自行車,她的人和思維都不斷地逡巡,對於自己喜歡的地方,她總是熟悉每一條隱秘小徑的曲折彎拐。其作品彩度低、內斂、不為人物或物件做細緻的刻劃,因而有較強的塊面繪畫性。她討論的是哲思: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人的本質是_____?
Welcome to the JUNGLE | POORBOY
Exhibition Limited Edition: Jungle Camera POORYBOY first ever instant camera ‘’JUNGLE Camera’’ will be available this Saturday.Come pick up the camera and join us to get lost in the JUNGLE together. "SAVE THE DATE: November 4th 2PM TPE" POORBOY 除了首次海外個展選定台灣當做第一站,同時也將首次發行即可拍底片相機 ‘’JUNGLE Camera’’ ,相機除了有藝術家親筆簽名之外,極度限量只限定100
INTERVIEW: TUNG-LUNG WU
[ 專訪 ] 藝術家 吳東龍 藝術家吳東龍的作品中,簡約的表象下隱藏著一場與美感的對話,一場與生命的辯證。底色的著墨、符號的琢磨,以及線條的安排和留白的鋪陳,都凝聚了他深刻而細膩的筆觸,帶著一股協調的感覺。從遠處觀賞,畫面中彷彿展開了色塊、符號和線條之間的對話,然而當你靠近作品仔細端詳時,那看似平和一致的底色卻蘊含著驚人的生命力。 世界已走出疫情的陰霾,但在舊世界的瘡痍之後,我們將走向何方?隧道盡頭的新世界又將是什麼?藝術家吳東龍先生的「隱外之境」個展將於2023年9月16日至10月21日在 Artemin Gallery舉行,展出其繪畫作品。或許這場展覽能為我們帶來一些靈感。
Beyond the Hidden 隱外之境 | 吳東龍
文 / 陳世霖 - 大提琴家與「ISM主義甜時」創辦人 世界似乎已走出疫情陰霾,但在滿目瘡痍的舊世界後,從此我們會走向何方?隧道盡頭的新世界會是什麼?或許這場在《Artemin Gallery》所策展的「隱外之境」能給我們一些靈感。 17世紀「啟蒙運動」以降人類逐漸脫離了中世紀的神學禁錮,在思想上開啟了現代化的進程;實驗科學的大步跨越、理性思維的深化;人們衡量著「人性」與「宗教」價值上的輕重,驗證、推理等眾多具系統性的方法論,催生了如哲學家笛卡兒 (René Descartes)、培根 (Francis Bacon) 與後來的康德 (Immanuel Kant) 對「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思辨,直到近代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對於「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討論、思辨也從未停歇。 在音樂藝術上,17世紀的德國作曲家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受「啟蒙運動」影響,在和聲 (Harmony)與對位 (Counterpoint) 技法的精彩應用,爲西方的「複調音樂」,也就是我們所熟知「古典音樂」 (Classical Music) 開啟了一頁璀璨篇章。當時「理性主義」的方興未艾的確將人類文明往前帶了一大步。 標誌性的幾何、色塊、線條、符號運用,台灣藝術家吳東龍的創作我們一直以來以「抽象」、「簡約」來定義。畫面上的鋪陳充滿著對理性的自覺,甚至對於畫作中畫布底色的處理、堆疊,也蘊藏著科學實驗般的假設、嘗試、驗證;對洗鍊畫面的呈現企求如平面幾何裡的畢氏定理 (Pythagorean theorem) 《a² + b² = c²》 或愛因斯坦著名質能等價公式《E = mc²》那般簡潔、和諧但也抽象。 然而如同音樂中無論是如何嚴謹、深思的曲式結構,藝術創作的本質終究在試圖傳遞藝術家對情緒、對人性、對生命的獨特觀點。樂譜上每顆精準寫下的每顆音符,是思考、意識、觀點、情緒在一段時間內的聚合與流動,音符存在的意義是為了意識與情感的表達。 東龍的作品中何嘗不是如此?底色的著墨、符號的琢磨,抑或對線條的安排、留白的鋪陳,在「簡約」表象底下是一連串與美感的對話、辯證,還有對生命的省思、質問,「簡約」與其說是創作的表現形式還不如說是那是種在面對自我後的解放。 在簡約、減法的過程抽離了具象,「抽象」兩字也就隨之映入了人們的腦海,也在這時讓一般人在面對作品時感到看不懂、感到生畏。別說現代藝術,就連古典音樂長久以來也是面對相同的窘境;音樂是時間的藝術,它本身就極為抽象,只單純由Do、Re、Mi、Fa、Sol、La、Si,七個音構成旋律、和聲,音樂聲響的出現與消失不過在數秒間,摸不著、看不見,在人的五感裡很難留下些什麼。 尤其在這裡教育普遍追求正確答案的我們,在欣賞抽象作品但腦海裡卻搜尋不到與之匹配的答案時那樣子的氣餒、不知所措,「抽象藝術太難我不懂」,這樣的沮喪時而可聞。但我們來聽聽作家沈從文怎麼說。 已故作家沈從文在家書中曾描述聆聽鋼琴家傅聰的演奏:「簡單幾個音符所傳遞的感情、畫面,我不知要用多少字才寫得出來、形容的出來。」 的確,不同形式的藝術呈現都是藝術家個人意識的轉化與展現,但聽著音樂的我們有意無意將自己的情緒經驗投射至流動的旋律中,無論是觸景傷情、懷古傷今;情緒的感受本就存在人類群體裡的普遍現象,差別只是每個人有著不同接受刺激的場景。因此無論音樂、美術、舞蹈
INTERVIEW: KABEKUI
[ 專訪 ] 藝術家 KABEKUI 在『Blink | 霎』展覽中,KABEKUI透過生活中的矛盾和美感尋找靈感,試圖連結自我內在與外在的世界,並藉由同名角色『KABEKUI』,傳達靈魂不受束縛、突破界限的概念,而複雜且交織的線條,象徵著生命的曲折與蜿蜒,探索人生中的轉折與變化。"讓我們一起發掘 KABEKUI 還不為人知的一面" Artemin: Who is KABEKUI?